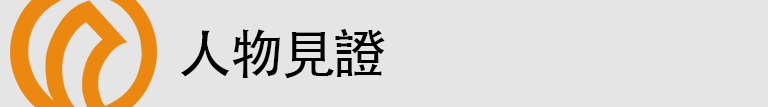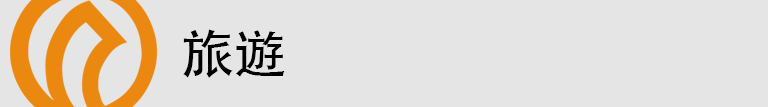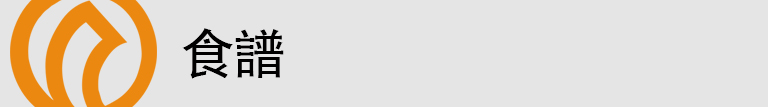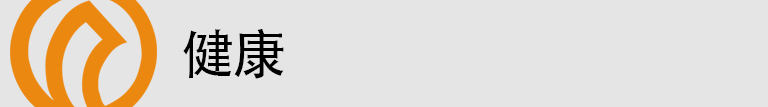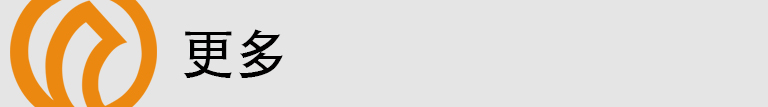2013年5月
文/李潤輝
「有一天,她或許會認不出你了。」一個朋友預測。在所有的人當中,母親是最後一個我以為會喪失思考能力的人。她具有我認識的人之中最敏銳的頭腦。就在我進入大學之前,我曾回到香港度假,那天我陪她去商店買海味,她買了大約八、九種不同重量和單位價格的海味。店主撥打著算盤算了半分鐘吧,然後說出一個總價。母親眯著眼睛想了一會對他說,應該是怎樣怎樣。店主又在算盤上算了一遍,結果要同意母親的數字。我不知道她是如何運算的,儘管那一年我在畢業試上囊括了校內兩項數學的第一名。
起初,沒有人注意到母親得了老人癡呆症。開始的時候只表現在一些小事情上,比如丟失了鑰匙或忘了把錢藏在什麼地方。此後不久,我們便帶她去看醫生,證實了我們最壞的猜想——她的確是患上癡呆症。母親逐漸失去協調能力,因為她體型較大,照顧者開始覺得很難應付。
認不出自己的兒子
每星期二,寶活(Burwood)區的救世軍大廳,都會讓出場地給當地的華人安老之家,組織老年人康樂活動。照顧者經常會帶母親去那裡。有一個星期二我正好經過寶活,於是臨時決定去看看她。母親坐在一群人裡聽故事,當她看到我走進門的時候,她先是茫然地看著我,然後緩緩地站起來朝我走過來。照顧者很快的上前攙扶著她。她走到我面前問:
「你是誰?」她盯著我問,面上沒有一點感情。
「我是妳的兒子——亞輝嘛。」
「我的兒子?真的嗎?」她低聲得好像在問自己。
「是的,當然是真的。」我擁抱著她,這次的擁抱裡她沒有笑。
「為什麼?為什麼你是我的兒子?」她仍是低聲地問。
「因為妳生了我,所以我便是妳的兒子咯!」
「那你為什麼不來看我呢?」
「我來,我常常來看妳的,但妳不記得了。」
她推開了我,又再看看我:「你是誰?」
「我已告訴妳——我是妳的兒子。」
「我有一個兒子?」她還是不笑。我又給了她一個擁抱。
「是的。妳有三個兒子、兩個女兒。」
「三……?那他們在哪兒?」
「他們住得比較遠。」
「為什麼他們不來看我呢?」
「他們來的!他們來看你……他們都陪你去飲茶!」
她再不會康復了
母親是在美國「9‧11」災難的前一天,進入療養院的;接下來的一年,她就在那裡度過。雖然她在那裡的時光短暫,但我對療養院的工作人員永存感激!
開始的時候她好像染上了感冒,幾天以後,工作人員又打電話告訴我說,母親要被送入醫院接受治療了。我趕出辦公室陪她到了醫院,最後她被診斷為肺炎。專科醫生給了我們一個壞消息——母親不會康復了。
「試圖救回她,只是延長這個難免的過程,並且導致不必要的痛苦,」醫生說:「管子只會讓她更加不舒服,灌輸的液體可能會凝聚在四肢,甚至進入肺部。」醫生建議摒除所有生命支持,使母親踏上必然的路!
「兩天沒有吃東西,病人便不感到饑餓。」醫生解釋說:「我會讓她注射嗎啡,以確保你母親感到舒服,並且她隨時會去的了。」
但母親持續著:一天、兩天、三天、四天……連醫生也一度失去耐心,要把母親送回療養院繼續等待——因為她遲遲不去。我就負起那痛心的差事,與醫生爭論,告訴她(醫生)不需要再等太久了。在內心深處我不斷問自己,我到底是希望母親死還是活呢?現實情況似乎使我站在醫生的那一邊。
「你今天還好嗎,媽媽?」這樣問使我很難受——我覺得很虛偽。在剛開始的兩天,當我問這個問題時,母親會稍微挪動一點點,或眨眨眼睛,我好像還見到她點了點頭,但這些反應後來便消失了。我低聲在她耳邊說:「我是妳的兒子,輝。我來看妳了。大家都很好,妳不必擔心。人人都愛妳,媽媽。我明天會再來看妳的,我每天都會來看妳。好好休息啊,媽媽!」
等兒女見最後一面
玲姊和晴妹於9月26日,從美加飛抵悉尼。那天,我們5人圍在母親病床周圍,告訴她我們愛她,我們現在都很好,她不用再擔心我們了。我用指尖張開她的眼睛:
「媽媽,妳看,我們都來看妳了。有玲姊、我亞輝、晴妹、佳弟、德弟,你所有的五名兒女都在這裡了!」
那天晚上半夜,刺耳的電話鈴聲衝破了夜晚的寂靜,母親去世了,我們趕到醫院去,圍在她的旁邊,太太Sally說,她知道母親肯定是為了再見我們全家人一面,才堅持了這麽多天的。
我至今仍經常夢到我的父母親,有時在夢中我會想到他們仍住在悉尼,而我卻忘記了去探望他們。在我的夢中,我充滿著內疚,擔心他們是否吃得好,就像母親從前經常擔心我們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