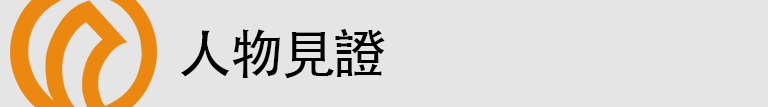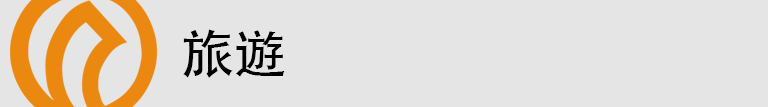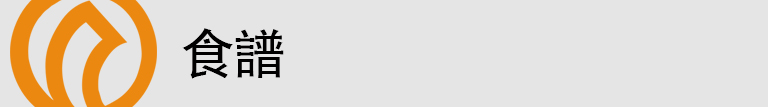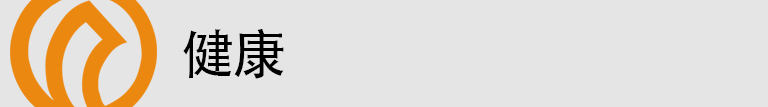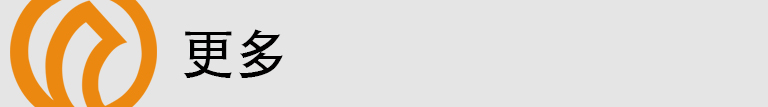2013年4月
文/賴黃婉群

走出自己的安樂窩,必須有很大的信心。
如果我告訴你,我要離開悉尼去非洲,你會同意我是在離開我的安樂窩。
悉尼是一個很好的地方──環境優美、空氣清新、風景如畫,有充足的社會保障和醫療福利,還有世界級的教育等等。
在這裡,我們有很多的同胞,有多份中文日報,可以一邊飲茶享受點心,一邊與同聲同氣的朋友聊天。我們暗地裏比較那些精英學校,為孩子籌劃將來的專業,期望他們成為醫生、獸醫、律師、驗光師、會計師或物理治療師等。
1986年,我們結婚還不到一年便從香港移居悉尼,即使當時是一週中只有週四晚可是延長夜購 (Late Night Shopping)的年代,我們需要開車到中國城,才可以飲茶或購買中國雜貨,我還沒感覺到自己會想家。
宣教士的鄉愁
1998年,帶著七歲的兒子和六歲的女兒,丈夫和我去到遙遠的非洲肯尼亞的內羅畢。聯合國在東非的總部就設立在內羅畢,同樣,我們的差會在此建立了聯繫非洲各國的樞紐,包括肯尼亞、烏干達、坦桑尼亞、蘇丹、埃塞俄比亞、中非、剛果、莫三鼻克和馬達加斯加等。我們有很多來自不同國家的同工,但華人宣教士同工只有寥寥幾個。
在我四十年來的人生中,這是我第一次感到有思家病!我渴望和我家人以外的人講廣東話;我非常渴望能品嘗一些中國的食物,即使我要支付四倍的價錢及要開車兩個小時才能夠買到。儘管是明日黃花的隔夜新聞報紙或陳年雜誌,我也希望能閱讀一些中文書刊!
其實,孩子們很早就安頓在我們差會辦的一所宣教士子女學校,對他們來說,這只是像到其他一所學校去繼續他們的學業和樂趣而已。我的丈夫顯光是一個很容易投入和賣力的人,他很快就沉浸在繁忙的事奉中,而我卻一直在睜大眼睛,尋找華人、中國食品或中文書刊!
首先,我們要忘記「煲電話」(長時間的在電話聊天),全肯尼亞的固網電話都是斷斷續續,而不是想用就可以用的,「重撥」是最常用的電話按鈕。我們幾乎要付茶錢給技術人員,他們才會來維修電話線;通過解調器發送電子郵件,這就成為我們的「救命線」了。難怪在非洲手機市場迅即淩駕固網電話之上,我很高興能看見高科技對他們有莫大的幫助。
買豆腐傳福音
惟恐非洲資源缺乏,我在抵達非洲半年前已經包裝好了四十五個箱子的物資,以船運寄往內羅畢,幫助我們的新環境增添色彩。在非洲的超市購物,雖然價格較高,也要果斷地決定買或不買,因為貨物一旦售罄,不會像在悉尼般立即補貨,可能要等幾個禮拜才能補貨上架!過了一段時間,因為家裡進賊,在警察局我們認識了一些中國大陸來的同胞,然後輾轉知道在什麽地方可以買到豆腐── 一些你不能船運過來的食物!我還記得,當我們進入這個製造豆腐的王先生的房子,他把豆腐從水桶中撈上來賣給我們,我們也可以從他的家居式的店鋪購買一些有限品種的中國雜貨食品,也和王先生和他的客戶交上了朋友,並把福音傳給他們。經過多年的耕耘,他們大部分已經受洗信主了。
適應當地生活
有時上帝關閉了門戶,但祂仍會打開一道窗口!我們學會了很多,作為宣教士,我們必須「FAT」──靈巧(Flexible)、適應(Adaptable)和受教(Teachable)。有一個宣教士同工給了我一本非常棒的烹飪書本,名為《或多或少》,讓我們懂得利用當地的食材來作日常烹調的菜式。那裡西蘭花很貴,但我們感謝神可以讓中國小白菜能在肯尼亞生長。在肯尼亞,我沒本錢吃五塊錢一個的奇異果(Kiwi),但你可能會嫉妒,我只花五分錢就能買到黃油果(Avocado)了!正如使徒保羅所說:「我並不是因為缺乏才這樣說:我已經學會了,無論在什麼情況之下都可以知足。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富裕;我已經得了祕訣,無論在任何情況之下,或是飽足,或是飢餓,或是富裕,或是缺乏,都可以知足。我靠著那加給我能力的,凡事都能作。」(《聖經》新譯本「腓立比書」第四章11-13節)
華人和印巴人
如果我留在悉尼,我會專注於享受中國文化的氛圍,而忽略其他種族的存在和需要。悉尼同樣是多元文化的社會,有從中東、印度、歐洲和其他地方來的人,但只是在非洲的時候,我才發現有這麽多的印巴人(印度和巴基斯坦人)。在當地人眼中,我們並不是「亞洲人」(Asian)。因為在當地,「亞洲人」只是指印巴人。華人就像「Nzungu」一樣,意思是「白人」。印巴人已經來了非洲好幾代,他們進入各階層的專業和生意。我們可以發現由印度人擁有的醫院、寺廟、商店、娛樂場所、賭場,甚至中國餐館。現在我們察覺到印巴人其實只是僅次於華人,是全球第二大的人口群體,且大有潛質超前。
把福音傳給中國同胞
我們花了很多年的時間來準備成為宣教士;在離開澳大利亞之前,我們需要接受跨文化培訓,在抵達肯尼亞前還要到美國接受進一步職前培訓;之後,還加上另外十二個禮拜的野外叢林露營和非洲語言及文化培訓,讓我們在新的國家有更好的裝備,以適應文化、生活和工作。然而,比開路先鋒還勇敢,那些中國大陸來的同胞,手上可能只有一筆小小的盤川、資本和一本中文拼音的學習英語書本,便大膽地走進非洲了。在當地,他們可能不太熟悉任何地理及文化環境,也可能舉目無親,但我可以說,他們的心理比我們宣教士還勇敢百倍,因為他們這樣離鄉別井,只有一個希望,就是為了賺錢。你可以想像,他們一般都很孤單,語言不通,也許經常被騙和面對困難重重等。感謝神!人的盡頭就是神的開始。我們與這些中國同胞建立了友誼,把福音傳給他們,他們大部分在中國從未接觸過福音,透過參加查考聖經班,很多是第一次聽聞福音,隨後接受了耶穌,受浸成為基督徒。
再離安樂窩
漸漸地,我學會了一些當地的語言,可以在當地街邊小攤,用超市一半的價格購買肉類蔬菜。當我幾乎適應了在內羅畢的生活── 住慣了房子,習慣了工作,熟悉了教會,疏通了支持網絡── 的時候,我又要再次搬遷了!搬家似乎是一個宣教士家庭的生活方式。
2002年,顯光在機構改組委員會參與如何有效把工場改組以迎合時勢所需,經議決後,我們在翌年安排到鄰國烏干達的安德培建立烏干達及坦桑尼亞聯合分部的總辦事處。安德培是與內羅畢相差很遠的小鎮,氣候比較炎熱;因為要依賴肯尼亞的海岸線,所以物資供應、食物和商品均較少,故此我是極不情願搬遷的,我不想再有任何的改變。
我的丈夫提醒我:「不要把內羅畢當作安樂窩!」。我的天呀,非洲豈會是安樂窩嗎?!是的,當你呆在一個地方,使你感到安全、舒適和不願改變,這裡就是你的安樂窩了。
我掙扎了良久,情緒抑鬱且波動不已,我想留在內羅畢,我很不願意接受新的挑戰。我很希望能保留我在內羅畢所擁有的物資,最終,我還是打了三十四個箱子,裝滿我的最愛物品,幫助我在恩德培── 一個接近機場,只是由四條街道組成的小鎮── 消遣渡日。
非洲人也守時了
驚奇的事開始發生了。在我快要搬離內羅畢之前,丈夫和我分別參加了弟兄和姊妹的查經團契(Bible Study Fellowship)。來到烏干達後,我渴望參加一些社交活動,甚至查經的機會,往返我要乘搭兩程小型巴士,當地稱為「Taxi」。BSF是在教堂裏舉行的,往返行程共要花三個小時。雖然非洲人說:「你有手錶,我有時間」,時間觀念與他們是不大相關的;嚴格及準時的BSF,卻給他們學會了守時。許多非洲人步行來參加,他們是何等渴慕神的話語!他們知道如果遲到了三次,便會被排在候補名單上。所以BSF不大像一般的聚會,大多數的人都要守時。這令我大開眼界,神的話語和誡命,可以解除文化的束縛。誰說非洲人不會守時?我可以放聲說「不!」因為我可以在BSF見證此事。
同工像個大家庭
在BSF,我遇到了其他兩位香港來的姊妹,每次BSF完畢,我們可以用我們的「白話」語言──粵語來聊天,也可以同時享受一下我們的長午餐。我很感謝他們的友誼,化解了我的思家病。
我們的差會宣教士同工也像一個大家庭一樣,雖然我以前曾在加拿大留學五年,還是回香港後在一家美國公司工作,才開始潤飾好我的英語,然後移民往澳大利亞工作;即使我們曾在澳大利亞人的教會牧會有數年之久,真正的多元文化接觸還是在非洲才開始,我們與來自二十多國家的宣教士一同工作,像是聯合國一樣。我們租住的寓所很接近辦公室,我們經常在辦公室舉行祈禱會。我們在邊境遇到了一宗嚴重的交通事故,在遠方的弟兄姊妹都為我們迫切地禱告,我們的宣教士同工更給與我們莫大的支持和鼓勵。從家裡到邊境要開車五個多小時,一位來自愛爾蘭的同事甚至願意放下繁忙的工作,跟我們到邊境的法院出庭,陪伴我們多走了額外的旅程來支持我們。
暫時的回家
2010年,又要搬家了,因為在澳大利亞的媽媽身體健康的緣故,我們預算有兩三年的時間返回澳大利亞── 我在香港以外的第二個家。這次我並沒有打箱,因為我知道在悉尼沒有什麽是買不到的。一個來自新西蘭的宣教士同工家庭,在十多年前抵達非洲的時候,只帶了幾件行李;十多年後,他們需要一整個集裝箱,把在非洲的家具物資運回家。我們剛巧相反,我儘量把所有的東西都留下來祝福當地的非洲人,只帶幾件在重量限額之內的行李回家。
當我去到最終的一個家的時候,我相信,我毋須再打箱包裝、不需要攜帶行李了,因為天父已經在那裏為我預備好了所需的一切!
(作者為電腦專業人員,移民澳洲悉尼後於1989年創辦「國際使者協會」,再移居東非宣教十多年,在差會擔任電腦訓練員、顧問及財務主任等職,因在悉尼的母親及本身健康欠佳,暫時調返悉尼。)